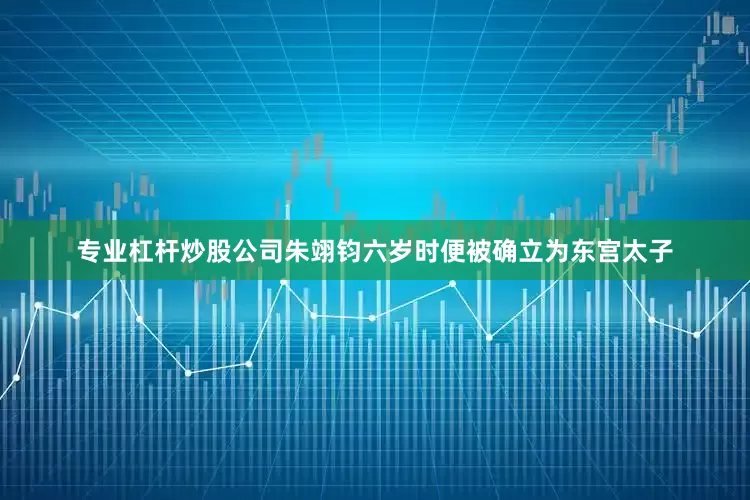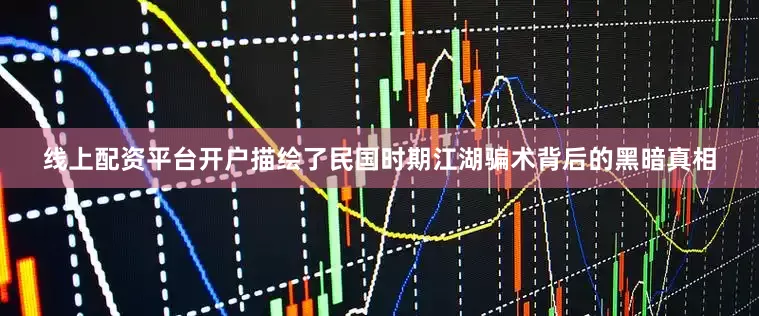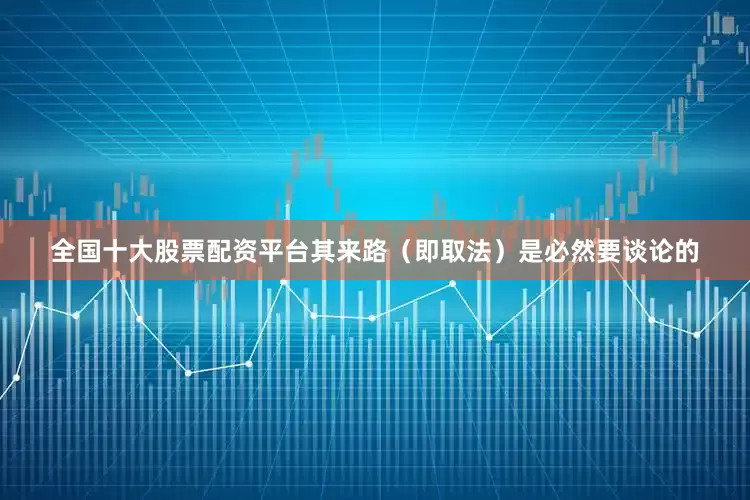
#长文创作激励计划#
以古为师,悉心交流!敬请关注收藏“大成国学堂”!在书法的历史长河中,苏轼堪称旷古罕见的巨擘,乃是 “宋四家” 当中极具表意风格的书家,他承继了锺王书脉,更是唐代书法传统的推进者。启功在《论书绝句》中评价道:北宋的书风,“苏黄为一宗,不肯受旧格牢笼,大出新意而不违古法。” 又言:苏轼的书法境界,“正如其诗所喻,绕树春风,化工同进者。” 此评语精准扼要地指出了苏轼变革古法、推陈出新、抒发胸臆、崇尚自然的书法特质。从这一角度而言,将苏轼视作北宋尚意书风的典型代表,实不为过。
图片
然而,有些美学家为突出苏轼对于文士心理的开创意义,竟断言:“苏的文艺成就本身并不高,…… 画的真迹不可复见,就其他而言,则字不如诗文,诗文不如词。” 此观点的臆断之处在于对苏轼书法自身及其变法意义欠缺一定的了解。
研究书家的艺术史,其来路(即取法)是必然要谈论的,而评判他的书法造诣,以及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其变通的途径及成果也必须明晰。但倘若深入探究,这里面尚有一些值得斟酌的关键之处。
图片
例如,取法的依据原本应当源于书家自身的陈述,或者弟子门生的记载,然而有时我们恰恰会发觉实际的风貌与文献的记述相互背离。再如谈到唐以后学书者的取法,依照惯例,通常会提及魏晋与唐代,作为两大书法源流,二者的区别是否应当明确?又如,论及一位书法巨匠的造诣,学者多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探寻深层次的根源,那么思想与书风之间的对应关系究竟如何?此类问题为数不少,情况亦较为复杂,倘若不加梳理辨析,我们对于核心问题的阐释定然难以如意。故而艺术史研究,广泛地搜罗材料、突破常规的思考、逻辑关系的重新构建乃是一种重要的方法。
图片
曾阅专文论述苏轼的取法与变法,采用了类似 “变法准备” 的标题。我认为,这属于一种行文的定式,凭借苏轼 “无意于佳” 的思维模式,定然不会为 “变法” 而刻意去做准备 —— 若如此,距离真正的变法创新,就相差甚远了。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苏轼的思想天地中,很早就存有不受束缚、力求创新的意识。这一点在叶梦得的《石林燕语》中记述得甚是清晰,一句 “想当然耳,何必须要有出处?” 已然展露了二十岁苏轼的超群才气与创造意识。在他早年研习传统经典的历程中,秉持敬畏、重视思变的观念是相互交织的。
图片
苏轼家学渊源深厚,学习书法极为勤奋,曾言:“方先君与吾笃好书画,每有所获,真以为乐。” 又道:“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锭,不作张芝作索靖。”(曹宝麟考订此语为苏轼早年所作)从他留存的众多论书文字当中,能够察见他对魏晋法书的敬畏之情以及对张、索、“二王” 等前辈贤达的追慕之意。
苏轼以 “精稳” 评价《遗教经》,以 “超然” 品评晋人帖,用 “高逸” 称赞王献之的书法,魏晋书法中恬淡萧散、从容不迫的精神乃是他品鉴书法的重要准则。在《题王逸少帖》一诗中,他对张旭与怀素草书疾速书写、故作姿态的方式予以批评。
图片
诗末云:“为君草书续其终,待我它日不匆匆。” 何为 “不匆匆”?即草书应当从容不迫地书写,这种富有林下之风、含蓄自然的魏晋书格是最受苏轼赞赏的。苏轼极为推崇陶渊明的作品,也曾以陶氏诗风来评价智永的书法,认为其 “精能之至,反造疏淡。”“精能” 是从法的角度,称赞智永书艺的精妙,而 “疏淡” 则是认为智永的书格达到了魏晋前辈恬淡自然的境界。
图片
苏轼对 “锺王” 书法评价甚高,认为 “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 那么在早年学书取法方面,他是否受到了 “锺王” 的影响呢?从现存的文字资料当中,可以发现众多其研习阅览 “二王” 法书的事例。如黄庭坚说:“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 又《仇池笔记》卷下中有 “硬黄临二王书” 一条:“王会稽父子书存于世者盖一二数也。唐人薛、褚之流,硬黄临仿,亦足为贵。” 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也提及:“(轼)幼而好书,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晋人,至唐褚、薛、颜、柳,仿佛近之。” 何为 “不及晋人”?自然是一种谦辞,但同样也表明了苏体与晋人的渊源。
图片
那么,苏轼对于 “锺” 的取法究竟如何?文献并没有直接的记载,然而从其二十二岁所作《奉喧帖》和三十二岁所作《自离乡帖》等作品中能够清晰地看到 “锺王” 的痕迹。尤其是《自离乡帖》与《钟繇存世小楷大合集》所收《白骑遂内帖》极为相似,“遂” 与 “动” 字几乎一模一样。而《自离乡帖》中的 “敢”“安”“在” 等字,横向舒展的笔画以及略带古拙隶意的捺画收笔,也彰显了锺书的特点。此外我们还发现,苏轼在竖勾、戈勾与竖画的起笔,横画的收笔上采用了逆重的处理方式。
图片
所谓逆重之法指的是起笔逆锋重按的书写方式,这种书写方式与 “锺王” 明显不同。“锺王” 笔触清简且自然,不论轻与重、藏与露、转与折,皆是顺锋而为。而在苏轼的书法中,逆回、逆藏的痕迹颇为浓重,这种书写习惯一直延续至他的晚年。此种笔法的形成或许更多源于唐人。从一定意义上讲,对于魏晋与唐人的书法取法,苏轼更倾向于后者。他认为到了颜、柳,不仅汇集了前代的笔法,更是在此基础上,“极书之变”,故而 “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锺、王之法益微。” 唐人开创了一种新变的规范,这种规范无疑对于重视思变的苏轼更具吸引力。
图片
苏轼对唐人书法的取法,通常会提及颜真卿、徐浩与李邕。黄庭坚在《山谷题跋》卷九《跋东坡自书所赋诗》中说道:“少时规摹徐会稽,笔圆而姿媚有余。中年喜临颜尚书真行,造次为之,便欲穷本。晚年乃喜李北海,其豪劲多似之。” 这段文献常被后世研究者反复引用,然而若仔细探究,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思索。其一,苏轼学习颜真卿是否是在中年(其终年六十六岁,中年至少应在四十岁以上)?其二,时人与后人屡次称苏轼学习徐浩,为何苏轼本人并不认同?从苏轼二十四岁所作的《奉喧帖》和三十岁的《宝月帖》(此帖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苏轼墨迹书作,见《苏轼尺牍墨迹合集卷》)中,能够明显看出颜真卿的影响。如《奉喧帖》中 “大”“奉”“书”“次”“意” 等字的笔意皆可见《争座位帖》的痕迹,而《宝月帖》中 “事”“及”“问”“胜” 等字的体势也显然是颜体。
图片
所以从苏轼的学书历程来看,他早年受到了 “锺王” 与颜真卿的共同作用,颜字宽博的体势、厚重含蓄的笔法,对苏体的最终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至于 “中年喜临颜尚书真行,造次为之,便欲穷本” 这句文献的内涵,并非指苏轼到中年才学习颜书,而是说经过长期的临池积累之后,他最为颜书清雄的气质所吸引,在临习中也更注重提炼颜书之 “神”。片刻之间随意临写一下,便将颜书之 “神”(“本”)展现了出来。
图片
对于取法徐浩的问题,苏轼自己不承认,他说:“昨日见欧阳叔弼,云:'子书大似李北海。’予亦自觉其如此,世或以谓似徐书者,非也!” 不仅苏轼自己不认可,苏轼之子苏过也是极力否定。他说:“(轼)少年喜二王书,晚乃喜颜平原,故时有二家风气。俗手不知,妄谓学徐浩,陋矣!” 这是一段公案。鉴于苏、黄如此亲密的关系,自然不会乱说,那为何他的观点会与苏家父子相互矛盾呢?
图片
黄庭坚云:“唐自欧、虞后,能备八法者,独徐会稽与颜太师耳。然会稽多肉,太师多骨,而此书尤姿媚可爱。……” 在黄庭坚看来,徐浩写得最好的也只是 “姿媚”,而通常情况则是 “多肉”。多肉微骨者被称为墨猪,而 “墨猪” 之讥正是苏轼最为忌讳的。
(待续)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我们将《苏轼尺牍墨迹合集卷》、《钟繇存世小楷大合集》精确复制,作为极其重要的“法帖3.0”藏本以飨书友!请注意,“法帖3.0”出品是原汁原味、无限接近原件超精复制品,不是网上通行的严重调色的低精度图片印刷形态!
欲购专业级《苏轼尺牍墨迹合集卷》、《钟繇存世小楷大合集》超清复制件的书友,可点击下面商品卡,品鉴与激赏!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举报。启恒配资-股票杠杆平台排行-正规股票配资开户-股票配资利息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